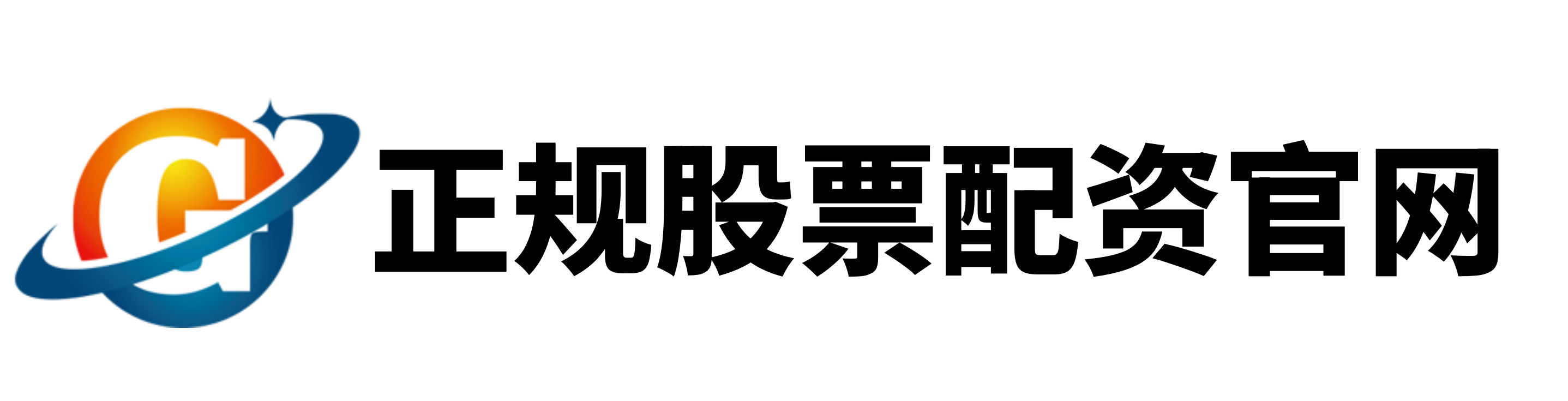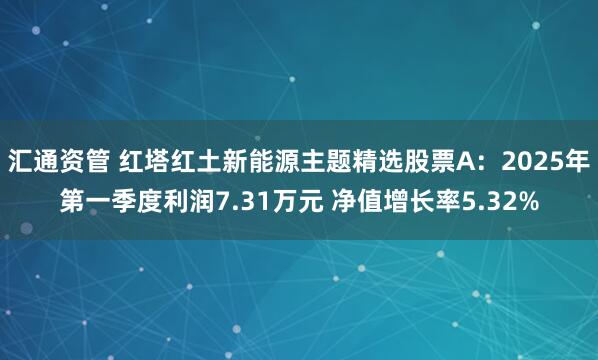杨方策略 你emo了吗?别自己抗!主动求助是守护心理健康的“良方”|健康素养66条

“最近总emo,是不是太矫情了?”“有点想不开,但跟人说多丢人啊,忍忍就过去了。”生活里杨方策略,不少人遇到心理困扰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要么自我否定,要么硬扛着,于是在持续的压力或坏情绪下,不仅感觉心累,还开始失眠、头痛、甚至容易生病。

过去,很多人常把心理问题归结于“想太多”或“性格脆弱”。但如今,脑科学与免疫学的研究已明确指出,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拥有真实的生物学基础。长期压力会改变我们的大脑结构,甚至会升高体内的炎症水平,直接增加疾病、糖尿病等躯体疾病的患病风险[1]。这意味着,心理健康不再是独立命题,它与我们全身的健康深度捆绑。
维护心理健康,因而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健康素养。《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年版)》第36条就明确指出: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遇到心理问题时应主动寻求帮助。
01 每15人就有1个抑郁,心理“感冒”或成当代最大“流行病”
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研究团队对全国32 552名成人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份、157个疾病监测点,此横断面调查显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焦虑障碍12个月患病率达4.98%——换算一下,全国约9500万成人正或曾受折磨,反映出抑郁和焦虑问题已成为我国成人常见的心理健康挑战[2]。
不仅仅是成年人,孩子更“卷”。《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3]。2023年《中国公共卫生》刊发了5省大样本研究,结果显示20 792名中学生中重度抑郁症状检出率19.7%,而接受过心理服务的比例低于10%[4]。
这些数字背后,是数以千万计正在经历心理困扰的个体,而其中获得专业帮助的比例却不足半数。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值得临床医生关注的是,心理健康与躯体疾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双向作用机制。
近年来,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不断证实,心理健康问题不仅仅是主观感受的波动,而是具有明确生物学基础的生理问题。2023年10月JAMA Network Open发表了一项跨研究,对83项fMRI研究(5 242名参与者、801个坐标)进行MKDA荟萃分析,发现既往暴露于慢性压力/逆境的个体,在广泛任务范式下均表现出杏仁核反应性增高,同时前额叶皮层(PFC)反应性减弱,这种“杏仁核过度驱动+PFC调控不足”的功能连接模式,与后续出现焦虑、抑郁症状的风险显著相关,该结果提示前额叶-杏仁核回路的功能耦合下降,可能是逆境削弱情绪调节能力、并产生持久心理健康易感性的关键神经机制[5]。
多项研究证实,长期的心理压力会通过神经内分泌机制影响免疫功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例如,持续的压力状态会导致皮质醇水平异常,进而引发胰岛素抵抗、血压升高等一系列生理改变[6]。这种心身交互作用的特点,要求医生需要在临床实践中必须将心理健康与躯体健康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02 求助行为的“神经激活”效应:重塑大脑的起点
当识别到心理问题的信号后,“主动寻求帮助”便成为决定健康走向最关键的一步。这不仅是健康素养的体现,其背后更有坚实的科学证据支持,证明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康复的开端。
主动求助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社会行为,前沿的神经科学研究揭示了其深刻的生物学意义。一项发表于《自然·人类行为》的研究通过脑成像技术发现,当个体做出“寻求社会支持”的决定时,大脑中负责奖赏、动机和决策的关键脑区——腹侧纹状体和前额叶皮层会被显著激活[7]。这种激活与在物质奖励中观察到的模式类似。这意味着,主动求助这一行为,本身就能启动大脑内部的积极反馈机制,为我们提供内在的神经动力,对抗由压力或抑郁导致的动机缺失和快感缺失。这从神经层面证实,“开口求助”不仅是向外界伸手,更是从内部启动了我们大脑的自我修复程序。
然而杨方策略,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常常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患者能够坦然承认自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却在谈论心理问题时讳莫如深。中国精神卫生的一项调查研究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缺口率高达64%[8],这意味着大多数需要帮助的人未能获得及时的专业支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其中病耻感是主要障碍之一,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污名化正在成为阻碍早期干预的重要障碍。

因此,在临床工作中,为大众普及主动寻求帮助的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越早求助,好得越快。2023年《World Psychiatry》系统综述(含17项前瞻性队列)显示,出现抑郁症状6个月内求助者,1年缓解率提高42%,迁延成慢性风险下降35%[9]。而且拖得越久,脑损伤越大。现有的研究表明,未经治疗的心理问题确实可能导致脑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并且这些变化可能随着病程的延长而加剧。多项研究已证实抑郁症与海马体积变化之间的关联,一项研究指出,慢性应激与海马体神经发生减少有关,这是一种与认知和情感相关的神经可塑性基本机制,与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密切相关。这表明,心理问题若长期未得到干预,其对海马体的负面影响可能持续积累。所以一定要向病人强调,求助≠“脆弱”,而是“自救”。
03 构建多元化的心理支持网络,现代心理干预
前沿科学的突破,最终要转化为临床实践与公众健康的切实福祉。对于医务工作者而言,首要任务是引导公众破除对心理问题的认知误区,其中最关键的,是去“病耻感”化。将心理困扰正常化为人类体验的一部分,如同我们会患感冒、会得高血压一样,是构建健康求助心态的第一步。研究证实,这种“正常化”的比喻,能有效降低病耻感,让求助行为变得自然。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为公众描绘一幅清晰、可行的“心理求助地图”。这幅地图应是多元和立体的:
初级支持层:包括社区全科医生(他们往往是发现问题的第一道关口)、可靠的心理热线(如国家心理援助热线)以及身边的朋辈支持。这一层级的核心功能是“识别”与“倾听”。
专业干预层:涵盖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心身科)门诊、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当问题超出一般心理困扰的范畴时,这里是进行科学诊断和系统治疗(包括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的关键场所。
自我管理层:这是可以融入日常的健康生活方式。例如,基于实证研究的正念冥想练习,被证实能显著降低焦虑水平;规律的身体锻炼,被证明能促进内啡肽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释放,其抗抑郁效果与某些药物相当。

现代心理科学的进步为我们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丰富、更有效的干预策略。今天的心理健康服务,早已超越了“谈心”的单一模式,形成了一套结合生物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综合干预体系[10,11]。
在生物干预层面,药物治疗理念已不断迭代。现代精神药物研究正朝着更具靶向性、副作用更小的方向发展。重要的是,公众需要理解,针对中度至重度的心理疾病,药物并非“依赖品”,而更像是为大脑神经化学失衡提供的“矫正器”,能为心理治疗创造稳定的生理基础。
在心理干预层面,认知行为疗法(CBT)、辩证行为疗法(DBT)等经过大量实证研究验证的疗法,能帮助个体重塑不良认知模式,提升情绪调节和压力应对能力。它们好比是给大脑做“思维健身”,通过系统训练,建立起应对困境的心理肌肉。
此外,干预的场景与形式也正变得无比多元。除了传统的面对面咨询,基于互联网的数字疗法(如经过临床验证的APP和线上治疗平台)提供了可及性更高的选择。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支持网络这一强大的“背景资源”。家人、朋友的理解与接纳,社区中的支持性团体,以及工作场所的心理健康促进计划,共同构成了个体心理康复的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 Mariotti A. The effects of chronic stress on health: new insights into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brain-body communication[J]. Future Sci OA. 2015 Nov 1;1(3):FSO23. DOI: 10.4155/fso.15.21.
[2] Huang Y, Wang Y, Wang H, et al.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J]. Lancet Psychiatry. 2019 Mar;6(3):211-224. doi: 10.1016/S2215-0366(18)30511-X. Epub 2019 Feb 18. Erratum in: Lancet Psychiatry. 2019 Apr;6(4):e11. doi: 10.1016/S2215-0366(19)30074-4.
[3] 傅小兰,张侃.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19-2020[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群学出版分社,2021.
[4] Zhou Y 等. 中国 5 省在校中学生自杀行为流行状况及其与抑郁、焦虑关联. 中国公共卫生, 2023;39(4):415-421.
[5] NikiHosseini-Kamkar, Mahdiehvarvani Farahani B , Majanikolic B ,et al.Adverse Life Experiences and Brain Function: A Meta-Analysis of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indings[J].JAMA Network Open, 2023, 6(11):20.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3.40018.
[6] Shimbo D , Cohen M T , Mcgoldrick M ,et al.Translational Research of the Acute Effects of Negative Emotions on Vascular Endothelial Health: Findings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2024, 13(9):12.DOI:10.1161/JAHA.123.032698.
[7] Bartra O , Mcguire J T , Kable J W .The valuation system: a coordinate-based meta-analysis of BOLD fMRI experiments examining neural correlates of subjective value.[J].Neuroimage, 2013, 76.DOI:10.1016/j.neuroimage.2013.02.063.
[8] Lu J , Xu X , Huang Y ,et al.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treatment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J].The lancet. Psychiatry, 2021, 8(11):981-990.DOI:10.1016/S2215-0366(21)00251-0.
[9] Cuijpers P, Miguel C, Harrer M, et al.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overview of a 'Meta-Analytic Research Domain'[J]. J Affect Disord. 2023 Aug 15;335:141-151. DOI: 10.1016/j.jad.2023.05.011.
[10] Borrione L, Bellini H, Razza LB, et al. Precision non-implantable neuromodulation therapies: a perspective for the depressed brain[J]. Braz J Psychiatry. 2020 Aug;42(4):403-419. DOI: 10.1590/1516-4446-2019-0741. Epub 2020 Mar 16.
[11] Nord CL, Halahakoon DC, Limbachya T,et al. Neural predictors of treatment response to brain stimulation and psychological therapy in depression: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19 Aug;44(9):1613-1622. DOI: 10.1038/s41386-019-0401-0.
智慧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优配网 郑晓龙新剧开机,周冬雨沦为配角,看到女主不少网友表示想弃剧
- 下一篇:没有了